在上班路上我骑自行车摔了一跤,飞到了马路中间。
这不是我第一次骑车摔倒了,2023年末的两个月,我好像被摔倒之神诅咒了,摔倒了好几次。上坡一次,下雪一次,停车一次。还有今天这次,明明坐垫已经被固定好了,我骑到半路上忽然杆子收缩,我重心不稳,摔飞在马路上,旁边一辆车呼啸而过。
我连滚带爬地拖着车离开了马路中央,很幸运没有被车撞到,但脑袋离汽车这么近还是把我吓到了。我忽然意识到我离受伤或者死亡这么近。
外公是第一个离我而去的亲人,他的逝去给我带来了极大的感触,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面对死亡。当我不是从书本、新闻中接触到死亡之后,我对死有了新的看法,从而投射到对整个世界的感知。
世界
死了就是死了,任你天花乱坠说出一堆意义,对于个体而言还是永恒的消亡。我深信世界的本质是无意义的,所有的意义都是人赋予的,将一个人的死定性为光荣、伟大,其作用更多是安慰还活着的人们,对已经死去的人来说,他也感知不到这些了。正是意识到生命的宝贵,死亡的可怖,我才更加敬佩那些英雄烈士,且不谈他们因何而死,但就他们连死都不怕,就足够让人心生敬意了。
数字很难承载死亡背后的重量,巴以冲突已经死了几万人了,近期日本的地震也死了几十人,但阅读到这些数字的时候,总感觉它们给我带来的冲击力是一样的,这是互联网时代信息流狂轰滥炸的弊端,人的神经已经麻木了。
当我具体地看这些新闻中死亡的个体报道,尤其是那些残肢断臂的照片时,死亡的气息扑面而来。这些死者的死状不尽相同,但他们的归宿是一致的,就是无声无息地死去。那些专门被报道的死者会好很多,我会注意到他(她)是谁的父亲(母亲)、谁的丈夫(妻子)、谁的儿子(女儿),这样他就从一个数字1变成了一个关系网络,死亡变得具象化。
曾经的我也像网络上的愤青一样叫嚣着“武统”,“留岛不留人”等等,在近两年关注了俄乌战争,巴以战争之后,我深切意识到战争的残酷。和平年代,战争离我们太远,死亡也变得抽象,战场上的士兵并不像红警里点30个动员兵,出了兵营就大喊“For mother Russia!”。他们是真切的人,有不同的人生经历,或许绝大多数并不波澜壮阔,但如果把一个人的人生事无巨细地编写成书,也够那些发动战争的无良政客读上三天三夜了。
所以战争永远是最后的手段,对和平温和的态度有时并不意味着软弱,而是体现出对生命的尊重与爱惜。
于个人
以上有关战争的思考主要是近一年来的积淀,而上班路上的这一摔给我带来的更多的是个人层面的感悟。
死亡是不可预测的,它不会和你提前打招呼,而是倏忽而至。我又想起了我的外公,他是我对死亡最初的经验来源,他死前一直念叨着还想再活几年,真是闻者伤心,听者落泪,然后再见就是棺材里露出的一角青灰色脸庞,最后就变成一个骨灰盒了。这一切都让人猝不及防,又显得顺理成章,一个人可以在平常的夜晚死去,在几天内就被抹去世间的痕迹,死亡来去匆匆。
我意识到自己在某一天也会死去,我不再预设这一天发生在七十岁或八十岁,而是明年,甚至明天。我有时会优柔寡断,缺乏行动的勇气,心里会产生待时机成熟我再去做的想法,那时我都会问自己,假如下周要死了怎么办,死了就没有未来可言了。
这并不意味着我处于对死亡惶惶不可终日的状态下,而是我意识到有常伴随着无常,人当把握当下的每一瞬间。
说死亡或许太过极端,用意外这个表达可能比较容易接受。我有时会幻想每个人的头顶上有两个数字,一个是生命倒计时,一个是相见的次数,我无法得知具体的数值,但它们一定是在减少的。比如我和爷爷奶奶过年回老家会见一面,老朋友定期一年会约几次,我甚至可以估算出数值范围是多少,而这些数字又可能由于逝去、离散而减少。这不得不让我去珍惜身边的亲密关系,见一面少一面也变得具象化了。
最后,还是觉得自己很幸运,这一摔没摔出个骨折、残疾,反倒是把脑子摔清楚了,希望在新的一年里能少些意外,平安顺遂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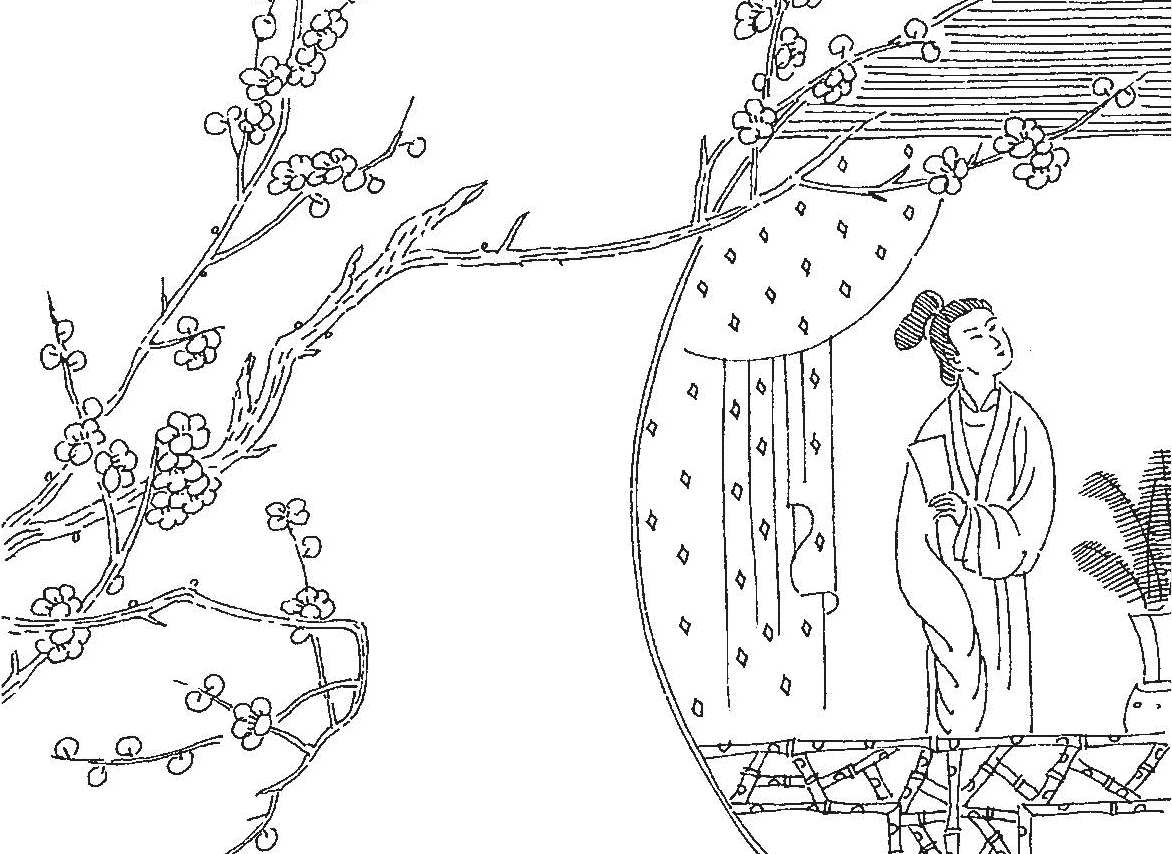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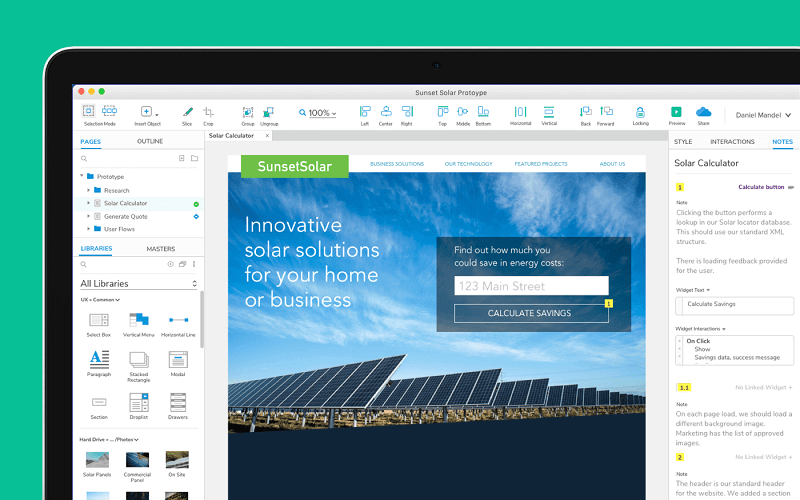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