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前
周五那天刷牙的时候接到防疫电话,告知我前两天坐地铁和阳性病例同车厢,要被封控了。当时一大早脑子意外地很清晰,先回忆那天有没有好好戴口罩,再给领导打了个电话申请居家办公,最后开始各种查找关于封控的相关资料。
捱到晚上一直处于等待通知的阶段,中途接到好几个电话,都是询问我这几天的轨迹。更准确地说是确认,他们似乎比我本人更清楚我这几天在哪里,不得不感叹当今时代人们的信息数据真的无所遁形。
晚上大概7点钟左右,来自社区的最后一通电话告诉我,我的码已经转红,要被拉到酒店隔离了。听到消息我就火速开始收拾行李,据说社区的人来之后是不会给时间的,家里的人知道消息都戴上了口罩,对我“如避蛇蝎”,让我离他们三尺远,场面回忆起来多少有点滑稽。
我忽然就想起了变形记里的萨姆沙,这家伙自从变成甲虫之后也是像过街老鼠一样的存在,但幸运的是,我还有重新修炼成人的机会。这个无比贴切的联想让我一时间心情大好,开始设想隔离期间能干什么事情,就且当成是一趟旅行吧。
隔离车没多久就来到了我的楼下,在上车之前我预想着和里面的人愉悦地交谈,分享一下彼此是在哪里密接的,如果很巧是在一个地方,还能互道一句密友。
刺鼻的消毒水味打断了我的思绪,刚上车几道警惕的目光就向我投射过来,他们觉得我很危险,那时我意识到他们也是高危人群,想吹牛逼的欲望瞬间就打消了。
狭小的车内加上我就四个人,大家都很默契地把脸对着车窗,蜷缩在角落里,对角的大叔像是刚刚下班,温柔地安慰家里人不要为他担心,听的出来他有一个岁数不大的孩子。另一角是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青年,好像是在打游戏,对周遭发生了什么并不关心。
隐约间我听见前座的那个妇女小声地抽泣着,继而嚎啕大哭,把车里的气氛营造地像我们坐上了驶往集中营的列车。直至她拿出了电话,对着电话那头苦苦哀求,我才明白她可能会因为隔离十天丢失自己的工作,原来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拿着电脑敲击键盘就可以上班的,隔离就意味着停摆。
世界的参差在这辆隔离车上显露无余,我看着窗外的灯火被拉成了一条长长的光影,统统抛在了车后,我们会被运向哪里,没有人给我们答案。
刚巧她哭累的时候,我们到了目的地,玄武湖旁边的宾馆,在一个小巷子的深处,位置相当隐蔽。我深吸一口外面香甜的空气,看了最后一眼夜晚的天空,还有些不想进去。自由就像水和空气,拥有的时候不曾发觉,直到失去,才明白它的珍贵。
隔离中
隔离的日子我简单总结为两个字——张嘴。张嘴做核酸,张嘴吃饭,循环往复,这样一天就过去了。饭菜每天都会有专人送到你的门口,但你总是见不到他们的人,以至于我总想守在门口逮住他们,却一直没能如愿。
兴许是为了填补隔离人精神上的空虚,饭菜还是比较丰盛的,一般是两荤两素带汤和水果,但你如果想疯狂星期四一下,那是想都不要想的,所以这段时间我一般会避开平时喜欢看的那些美食探店视频,以免给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带来困扰。

在这里最大的困难其实就是见不到人,一天到晚也说不了话,这和在外面沉默寡言不同,当你被迫安静的时候,你可能就想拉着一个人说上一天的话。没到这里之前,我没发现自己表达的欲望如此强烈,我排解的方法就是唱歌,一边码字,一边开着音乐放声歌唱,我一遍又一遍刷着歌单,在这几天里,竟然学会了好几首新的歌曲。
隔离好像也并非全无好处,因为斩断了外界的联系,难得会静下心来做一些以前耐不住性子的事情。安静地看一些摄影教程,重新捡起以前看不下去的书,把今年发生的一些事情复盘,这些整块整块的时间自上班后就变得相当珍贵,隔离的日子里我可以自由徜徉在自我的世界里而不用担心被一个电话打断。
最后就是我迫切地渴望健身,我和很多同事不太一样,他们回到家就瘫在床上身心俱疲,但我感觉我大脑和身体是分开消耗的,每次下班的时候精神倦怠但肉体特别亢奋,浑身有力没处使的感觉,总想找个地方把这股劲释放掉,让精神和肉体的消耗达到平衡。现在我觉得这两者已经失衡了,我迫切地想在街道上狂奔,让脚板亲切地接触地面,每一下和柏油路碰撞的快乐都将通过我的腿传导到全身,直达灵魂深处。
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外面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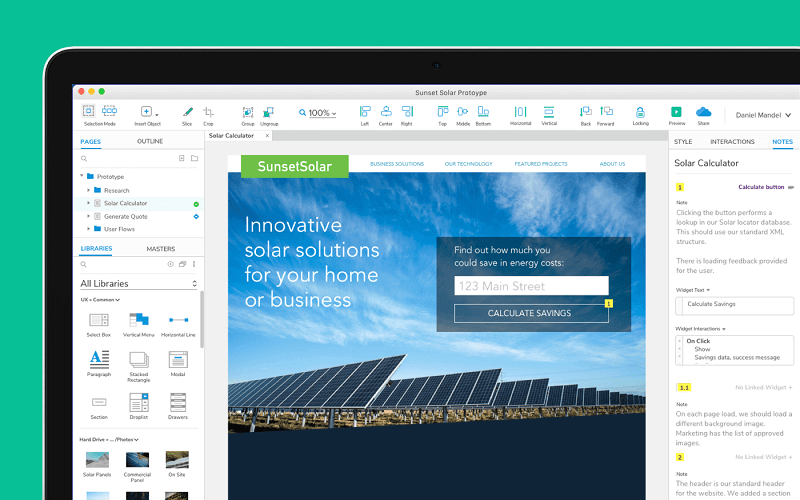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