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一个人应该是不会回河西的,因为我清楚地明白那些被修饰、美化过的记忆才是最美好的,而这些五彩斑斓的泡泡一旦被现实之光照射,会消散大半。这倒不是说我对母校有什么负面情绪,相反,这里曾经记录下我青春中大多美好故事,不愿回去只是怕物是人非,徒增感伤罢了。
这次是被老同学约着一起参加金陵河西二十周年校庆,就当是回去“做梦”好了,说是做梦是因为梦介于虚幻与真实之间,与现实泾渭分明。
怯的情绪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宋之问这首诗能流传千古,正是因为他写出了返乡中那种幽微、复杂的心理活动,我认为这句用在我返校也是再贴切不过了。和同行的老同学一样,我不太想与过去大多数老师再有什么交流,或许是见面只能无谓地寒暄,或许是本就与他们交情不深,或许是怕从他们斑白的鬓角中品味到世间无情是时间。我们更想当一位观众,静静地在河西“路过”,千般所想,皆被一个“怯”字说尽。
我始终认为一段回忆的主体对象是人,而空间、物品仅作为承载人活动痕迹的客观存在,哪怕是不在金陵河西,同一批老师、同学也能发生相同的故事。但事实上,人已经变了,我这里不仅指故人再难相聚,也指个体相较过去的改变。
改变不一定是坏事,有的人无论是为人处世还是专业素养都变得更加优秀。回到过去也不一定是好事,就像我在河西的路上抓住一个高三学生,他大概率会和我抱怨学业的辛苦,迫切想快点毕业。我想表达的是,我们这样一群人在同样日新月异的河西校园,只能不断怀念、怀念、该死地怀念,这给我带来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我很难对着在教学楼装满电梯,食堂充满了自动化设备,宿舍设计精致而考究的河西校园去回想往日的校园生活,我记忆中锚定的坐标已经在岁月潮汐的推动下发生了偏移。回望过去,除了星星沙砾般的记忆碎片,便剩下一片模糊。
我终于明白这感伤情绪与河西无关,是岁月,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岁月,悄无声息倏忽而至的岁月。它在绝大多数时候都不可感,是人影子的影子,只会潜伏在暗处,待你故地重游时,予以你痛击,原来已经过了这么多年。
心的圆满
相比于那些学校组织的晚会、校友会,我更喜欢在校园里漫无目的地走走。台前慷慨激昂的演讲、精彩纷呈的节目都是对外展示的官面文章,它们都不是校园最本真的模样。我想看的是那些伏在桌面上学习的身影,女同学抱着书穿行走廊,男同学天真烂漫地说一些俏皮话,这些才是我想象中的校园生活,而这些我在郭老师办公室感受到了。
一进郭老师的办公室,正好看见他在帮学生排练诗朗诵节目《我的南方和北方》,偏巧这是我学生时代非常喜爱的现代诗,在那一刻,我才又重新找到了当学生的感觉。我很羡慕这些朗诵时的学生,他们毫无顾忌地输出自身饱满的情绪,用清澈的声音和真挚的情感,将诗歌的韵律和意境传递。
我也随他们默念,恍惚间让我想起我曾在校园路上朗读海子诗歌的日子。那时我还不会用令人怀念来形容学校生活,诗歌是缓解压抑学习生活的解药,我一遍又一遍地念《太阳和野花》,把日子念得鲜活,我一遍又一遍地写《活在这珍贵的人间》,把生活写得柔软。
时隔多年,诗意的光芒又照耀在我身上,那股力量再次消解了我灵魂的颓唐。我确信我又回到了河西,不单是肉体行至,更是心的回归,从一个看客变成了参与者。

我这次来很大一部分目的就是回来看一看郭老师,站在他旁边我又回到了当年谨小慎微的模样,一时间讷讷无言,可见记忆虽然模糊,身体依旧诚实。郭老师是唯一令我又敬又怕的老师,这源于当年他对我的宽恕,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这种力量竟是这样强大,让身处叛逆期的我心悦诚服,不至于走上歧路,所以我对他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我试图向他展现我工作后成熟稳重的一面,让他明白我已不是曾经那般顽劣。我亦向他展示了我最好的诗词作品,证明毕业后我也有学语文,仍有好好读书。他夸赞我有了长进,作品也颇有章法的时候令我欣喜不已。那一刻,我才明白我多想获得老师的肯定,完成了这件事让我此行有了圆满的感觉。
在回去的路上,我给了街边卖唱的小哥一些钱,点了一首《突然的自我》,我动情地和他一起唱着。我很高兴,这让我想起高中KTV那段快乐时光,唱到一半,我挥手与他作别。”那就不要留,时光一过不再有“,这歌声送我到麦当劳,送我到地铁站,送我穿过通道,回忆河西的温柔,走向人生的春夏秋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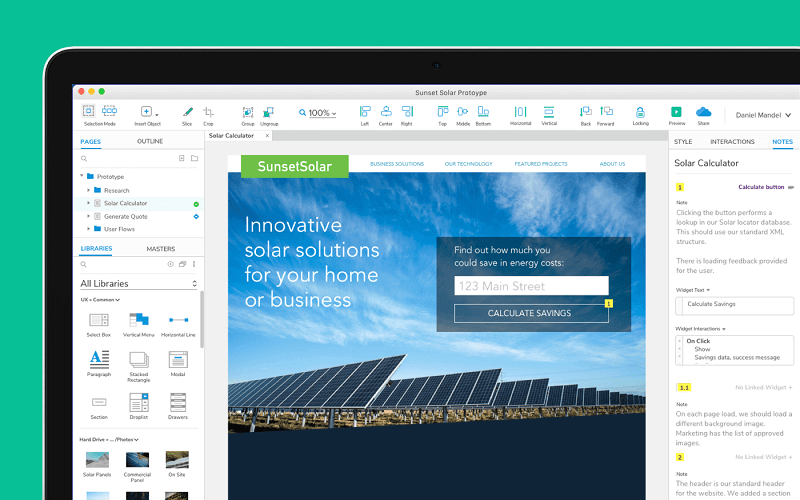





如果写河西的人、事、景,我估计大几千字都打不住,但当我试图表达这种复杂的情感,就有些吃力了。